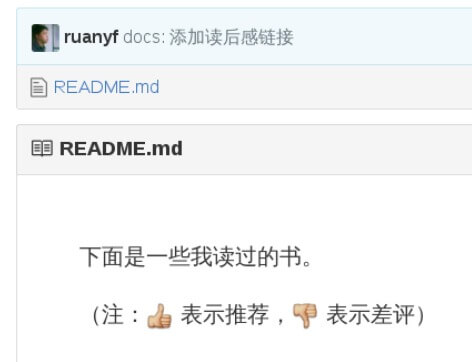库切的《青春》
上周,我整理了过去几年读过的书,做了一份书单。
然后,发现自己好久没写读后感了,上一篇还是两年多前的《做学问的八个境界》。过去几年,这个博客已经偏向纯技术了。虽然今后也会如此,但我觉得,读后感还是应该坚持写下去。
今天就介绍,我最近读完的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《青春》。

这本书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南非作家库切的"自传体"小说。

它讲述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年轻人,大学毕业后,为了逃避南非的种族对立,独自一人来到伦敦追求理想的故事。小说内容跟库切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,但又有艺术加工和虚构的部分。读来让人觉得很真实,但又像在听故事。
整本书都是约翰的内心独白,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。他讲述生活中的各种遭遇,然后倾述自己的内心感觉。自己提问,自己回答。如果你喜欢曲折的情节,大概不会喜欢这本书。但是,如果你对探索精神世界有兴趣,尤其是有过精神苦闷,那么你会爱不释手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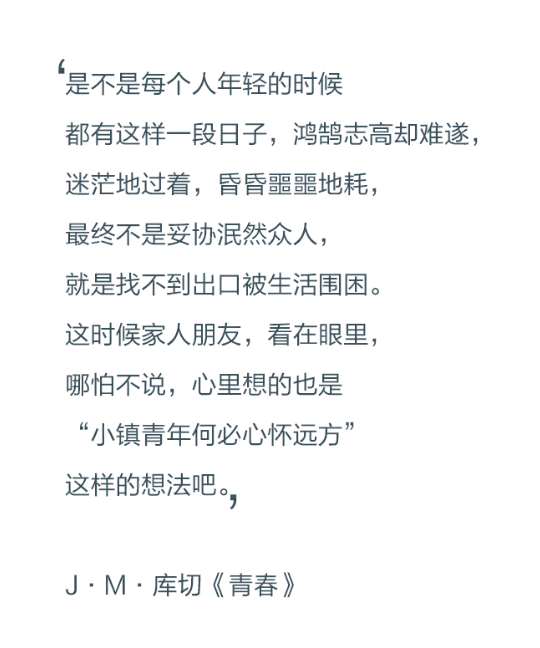
约翰爱好文学,希望成为一个诗人或者艺术家。但是,他来到伦敦后,只找到一份IBM公司程序员的工作。
面试官想知道的第一件事,是他是否永远离开南非了。
是的,他答道。
为什么?面试官问。
"因为那个国家要发生革命了。"他回答说。
约翰很快发现,IBM公司的这份工作,根本就在扼杀自己的生命力。
"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,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痛苦。惊恐会向他袭来,他费力地将其击退。在办公室里,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受到袭击。办公楼是一个毫无特色的玻璃水泥大厦,似乎散发出一种气体,无色、无味,一直钻进他的血液,使他麻木。他敢发誓,IBM在杀死他,把他变成一具僵尸。"
他在伦敦的生活也很糟糕,因为没钱。
"他在伦敦北部牌楼路附近的一所房子里,独自租一个房间住。房间在三楼,能够看见水库,有个煤气取暖器和小凹室,里面有煤气炉灶和放食物及碗碟等用品的架子。在一个角落里是煤气表,你放进去一个先令,得到价值一先令的煤气供应。"
"他一早就离家,回来得很晚,很少看见其他的房客。他在书店、美术馆、博物馆、电影院里度过星期六。星期日他在房间里看《观察家报》,然后出去看个电影,或到荒野去散步。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是最难熬的。那时,寂寞感会传遍全身,和伦敦的阴沉多雨的灰色天气、冰冷铁硬的人行道合在一起。"
在冰冷的现实面前,他原来的人生计划很快就破灭了。
"原本,他来英国时,心底里计划就是找个工作,攒点钱。当他有了足够的钱就放弃工作,献身于写作。积蓄的钱花完了就去找个新工作,如此等等。"
"很快他就发现,这个计划是多么幼稚。他在IBM的税前工资是每月六十英镑,他最多能够存下十英镑。一年的劳动能够为他挣得两个月的自由,而这其中的许多时间还得花费在寻找下一个工作上。南非 给他的奖学金只够勉强交学费。"
"而且他还得知,他不能够随意自由地更换雇主。管理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的新条例规定,每一次改变就业都需得到内政部的批准。禁止闲散无业,如果他在IBM辞了职,必须很怏找到別的工作,要不就必须离开英国。"
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。
"他觉得自己像个狄更斯小说里厌倦无聊的小职员,成天坐在凳子上抄写发霉了的文件。惟一打破一天的单调沉闷的是十一点和三点半。这时,送茶的女士推着小车,在每个人面前啪地放下一杯英国浓茶("给你,亲爱的")。"
"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巨大而冷漠的城市里,在这里仅仅为了能活下去,就意味着需要永远死命拼搏、力求不要倒下?"
"他暗自想到,我们要为了精神生活而献身吗?我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深处的这些孤独的流浪者,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?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,还是说精神生活就是它本身的报答?"
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时期,他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。
"他给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写了一封信。既然他猜想中国不需要计算机,就没有提计算机编程的事情。他说自己准备到中国去教英语,作为对世界斗争的一个贡献。工资多少对他并不重要。"
"他把信寄了出去,等待答复。与此同时,他买了《自学汉语》,开始联系汉语那陌生的咬紧牙齿的发音。"
"一天又一天过去了,中国人没有答复。英国特工截下了他的信销毁了吗?他们截下并销毁所有寄往中国大使馆的信件吗?如果这样,允许中国人在伦敦设立大使馆有什么意义呢?或者是,在截下了他的件以后,英国特工有没有把他的信转到内政部,并附上一张条子,说在XX计算机公司服务的那个南非人暴露出了他具有的共产党倾向?他会不会因为政治丢掉工作,被驱逐出英国?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,他不打算对此提出质疑。这将是命运的声音;他准备接受命运的决定。"
他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怀疑,自问追求的东西是不是错了,要不要放弃理想。
"这是一个他可以逃避的世界----现在逃还不晚,或者与之和解,和他看到的周围的一个个年轻人那样,满足于婚姻、住宅和汽车,满足于生活能够实际提供的,把精力放进工作之中。他懊恼地看到,讲求实际的原则多么奏效。"
他与不同的女孩交往,频繁地发生性关系,为了不让自己被苦闷淹没。但是,还是无法摆脱深入骨髓的孤独感,以及对未来的无力和迷惘。
"在泰特画廊,他和一个他以为是来旅游的女孩聊了起来。她相貌平平,戴副眼镜,身体结实,是他不感兴趣的那种女孩,但很可能他自己就属于那种人。她告诉他她叫阿斯特丽德,来自奥地利----是克拉根福,不是维也纳。"
"原来阿斯特丽德不是旅游者,而是个以干家务换取在主人家吃住的女孩。第二天,他请她出去看电影。他们的趣味很不相同,这点他立刻就看出来了。然而当她邀请他一起回到她工作的人家去的时候,他没有拒绝。他看了一眼她的房间:一间阁楼,蓝色方块布窗帘和颜色相配的床罩,枕头上靠着一只玩具熊。"
"后来,他再一次邀请阿斯特丽德出来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原闵,他说服她和他一起回到他的住处。她还不到十八岁,还有点胖乎乎的娃娃样。他从来没有和这么年轻的人在一起过----其实她还是个孩子。他给她脱衣服的时候,她的皮肤摸上去冷而黏湿。他已经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。他没有性欲。至于阿斯特丽德,虽然通常女人和她们的性需求对他是个谜,他确知她也没有感到有性欲。但是他们两个已经走得太近,欲罢不能,因此就干到底了。"
"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,他们又一起过了几个晚上,但是时间永远是个问题。阿斯特丽德只有在主人家的小孩上床睡觉后才能出来,在返回肯辛顿的末班火车之前,他们最多能有匆忙的一个小时,有次,她大起胆子和他过了一整夜。他假装喜欢有她在,但事实上他不喜欢。他单独睡觉睡得好些,有人和他同床。他整夜紧张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,醒来时筋疲力尽。"
"有好几个星期,他没有和阿斯特丽德联系了,她来电话了。她在英国的时间巳经结束,要回奥地利的家里去了。"我猜我不会再见到你了,"她说,"所以打电话和你告別。"
"她尽力就事论事地说话,但是他能够听出她含泪的声音。他愧疚地建议见一面。他们一起喝咖啡;她和他一起回到他的房间里过了一 夜(她称之为"我们最后的一夜"),紧紧依偎着他,柔声哭泣。第二天一早(是个星期日),他听见她悄悄下床,蹑手蹑脚地走进楼梯平台处的卫生间去穿衣服。她回来的时候他假装睡着了。他知道,他只要稍作暗示,她就会留下来。如果在对她表示出关心之前他想先做别的事情,比方看报纸,她就会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等着。在克拉根福,女孩子在行为举止上似乎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:不提出要求,等待着男人准备好的时候,然后为他服务。"
"他很想对阿斯特丽德好一些,她是这徉年轻,在这个大城市里是这样孤单。他很想给她擦干眼泪,逗她笑;他很想对她证明,他的心肠不像看上去那么冷酷,他能够用自己的乐意回应她的乐意,乐意像她希望被搂抱的那样搂抱她,倾听她讲述的关于她在老家的母亲和兄弟们的故事。但是他必须小心谨慎。过多的热情她就可能把票退掉,留在伦敦,搬来和他同住。两个失败者在彼此的怀抱中躲避,彼此安 慰:这个情景太令人羞辱了。要是这样,他和阿斯特丽徳还不如结婚, 然后像病人般互相照顾,度过一生。因此他没有作出暗示,而是躺在那儿紧闭着眼睛,直到听见楼梯的吱咯声和前门咔哒一声关上。"
这样日复一日,他过着这种毫无希望、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生活。他知道,自己必须做出改变了。
"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等待他的命运之神到来。命运之神不会在南非来到他的身边,他对自己说,它只会在欧洲的大城市之中。他在伦敦等待了几乎两年,受了两年罪,命运之神没有来。"
"他心里明白。除非他促使她来,否则命运之神是不会来找他的。他必须坐下来创作,这是唯一的办法。"
小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
现实生活中,库切从IBM公司辞职,离开了英国,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,从此走上了作家的道路。
(完)